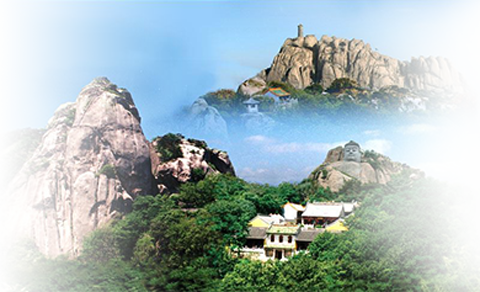【案情】
2019年1月,被告建筑公司从被告国土局承揽了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第十标段建设工程。后被告建筑公司将上述工程整体转包给了被告隋某,隋某后又将该工程整体转包给了原告,退出了涉案工程。工程结束后,原告与被告建筑公司、隋某就工程管理费扣缴比例发生争议。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被告建筑公司、隋某在扣除 5% 管理费后支付工程尾款 42万元,并要求被告国土局就尾款 10万元承担连带给付义务。被告建筑公司以其与被告隋某约定的管理费比例为15% ,且其三方转包系非法转包、转包合同无效为由,拒绝支付剩余工程款;被告国土局则以其并非合同相对人为由,拒绝支付工程尾款给原告。
【分歧】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转包合同无效情形下,实际施工人是否有权代位请求发包人及非法转包人支付工程价款。对此,存在以下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实际施工人无权代位请求。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实际施工人并非合同另一方且在合同无效情形下,实际施工人不具备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法律基础;
另一种意见认为,实际施工人有权代位请求。基于债权人代位制度不能充分保护实际施工人的利益,应当赋予实际施工人在特定条件下的代位求偿权。
【评析】
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基于我国建设工程审判实际及现实社会中层层转包情形突出这一状况,在《民法典》实行生效前,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29出台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现已失效)首次提到了“实际施工人”这一概念,明确实际施工人系相对于合法的承包人而言,是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借用资质等行为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实际履行施工义务的民事主体。在建设工程多次转包或分包后,实际施工人特指最终投入劳动力、资金与材料进行工程建设的人。现行的《民法典》及2020年12月25出台的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下称《解释》)对这一概念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
二、 代位求偿权最初特指我国保险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系指保险人依法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向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依据《民法典》第157 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司法实践中,实际施工人与非法转包人等签订的合同被认定无效后,该非法转包或违法分包合同的相对方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实际施工人。但基于建设工程的特殊性,不存在返还原物的可能性,因此,仅依据《民法典》的该规定,实际施工人无法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请求支付工程款。对此,新《解释》的第44条的规定赋予了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要求发包人、转包人及非法分包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权利,旨在保护建设工程合同无效情形下实际施工人的利益。
三、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实际施工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情形是需要严格审查的。新《解释》第43条第二款规定:“ 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可见诉讼时要先有证据证明发包人欠付工程款,实际施工人方可起诉发包人。同时,对代位求偿权的范围也应作出一定限制,笔者认为在面对具有群体性的农民工起诉讨薪时,可以要求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而对于个别的不具有代表性的少数人讨薪时,还应以普通劳务纠纷为由进行审理较为合适,而不应随意扩大发包人责任范围。因此,在建设工程合同案件审理中,应遵循该类案件的特殊规定,不能简单套用代位权的思维。
郑磊 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