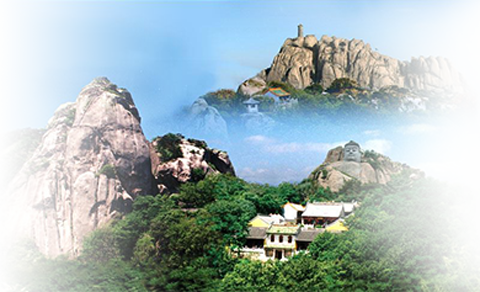共同犯罪案件中如何认定“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王学文
【案 情】2014年10月12日18时许,刘某在某镇某村西山上与被告人宋某甲之妻因故发生争执。次日上午 7时许,被告人宋某甲打电话将此事告知其儿子宋某乙。被告人宋某乙于10月13日上午 10时许回到家中,准备带其母验伤,因担心被告人宋某甲在山上再遇到刘某,遂上山找宋某甲。在西山附近,被告人宋某乙手持事先准备的平柳木棍与手持铁锨的刘某相遇并厮打,其用平柳棍对被害人刘某腿部和身上其他部位乱打。厮打过程中,刘某因看到宋某甲手持木棍赶来遂往山下跑,被宋某甲截住。宋某甲手持木棍对被害人刘某腿部、背部及身体其他部位进行击打,致被害人刘某背部、臀部、四肢等处广泛软组织损伤、皮下淤血并可见中空性皮下出血,创伤性休克导致呼吸循环衰竭,经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
2014年10月13日,被告人宋某乙报案称其已将伤害其家人的刘某抓住。宋某乙到案之初和侦查阶段均仅仅供述自己殴打被害人的犯罪事实,未供述其所知的同案犯宋某甲的共同犯罪事实,直到第二次开庭才如实供述其所知的宋某甲动手殴打被害人的犯罪事实。被告人宋某甲于2014年10月15日到侦查机关投案,基本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分歧】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宋某乙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并构成自首?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宋某乙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但其供述称被告人宋某甲没有动手,把相关罪责都揽到自己身上,是出于对其父亲宋某甲的保护,符合中国“亲亲相隐”的传统,可以从宽认定为自首。
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宋某乙到案后仅仅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拒不供述其所知的同案犯宋某甲的犯罪事实,直到其父亲宋某甲作了相关供述之后,其被迫作出如实供述,不符合共同犯罪自首的认定条件,不能认定为自首。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应从交代事实对定罪量刑的影响认定被告人是否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对于犯罪事实是否属于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除了要看该犯罪事实是否属于犯罪构成事实,还要看该犯罪事实是否对量刑产生重要影响。尽管本案被害人已经“死无对证”,但是根据被告人宋某甲、宋某乙所供述殴打被害人身体部位、力度、作案工具等情况,结合被害人刘某尸检报告以及从被告人宋某甲作案用的木棍上检出被害人组织成分的事实和有关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被告人宋某甲、宋某乙均积极实施了伤害被害人刘某的行为,且经查被告人宋某甲的犯罪情节明显重于宋某乙的犯罪情节。因此,宋某乙到案后仅仅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拒不供述其所知的主犯宋某甲的犯罪事实,且其未交代的犯罪事实对定罪量刑的影响明显大于已交代的犯罪事实,故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二、应从交代同案犯关联事实的程度分析被告人是否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共同犯罪人自首时,除了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外,还需交代其所知的同案犯实施的共同犯罪事实。被告人宋某乙到案之初仅仅供述自己对被害人实施殴打行为,不供述其父宋某甲对被害人实施过殴打行为,且一味坚持被告人宋某甲没有动手,把相关罪责都揽到自己身上,这种行为实质上是为了反驳起诉书对其父被告人宋某甲的指控。虽然中国历来有“亲亲相隐”的传统,新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父母、配偶、子女具有强制到庭的豁免权,但这些传统和法律规定并不意味着不交代其亲属犯罪事实能具备法定从宽处罚的条件。据此,可以认定被告人宋某乙没有如实供述同案犯的主要犯罪事实。
三、应从如实供述的时间节点分析被告人是否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刑法设立自首的初衷,在于鼓励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认罪、 悔罪,真正将自己主动交付于司法机关监管。如果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时间节点是在其他同案犯已作相关供述之后,是被迫作出如实供述的,那么其在实质上就不具有主动交付于司法机关监管的意愿,故不能认定为自首。
本案中,被告人宋某乙案发后虽主动报案,并在现场等候处理,但其到案之初和侦查阶段均未能如实供述其所知的同案犯宋某甲的共同犯罪事实,甚至否认、掩盖宋某甲的犯罪事实,直到第二次开庭才如实供述其所知的宋某甲动手殴打被害人的犯罪事实,反映出被告人宋某乙具有包庇或帮助宋某甲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心态,不符合自首的设立精神,故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