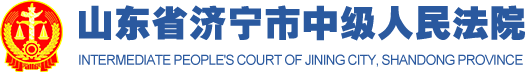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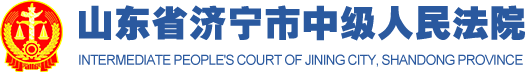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取消前置程序的司法应对(三) |
||
| 来源: 发布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 ||
|
四、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的协同 前置程序将行政处罚决定与民事诉讼的启动直接对应起来,客观上实现了行政处罚与民事诉讼的协同性与联动性。前置程序取消后,民事诉讼的启动不再以行政处罚为前提,这样实践中就可能出现诸多貌似又或者确实需要行政与司法相协调的诸多似是而非的情形,例如:投资者先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判定构成虚假陈述,行政机关是否必须开展调查?民事诉讼与行政调查同时进行,法院判决不构成虚假陈述,行政调查应如何处理?民事诉讼与行政调查同时进行,行政机关认定不构成虚假陈述,法院应如何处理?投资者申请法院向行政机关调取正在调查程序中的证据,行政机关应如何处理?法院认为需要以相关行政调查结果为依据,是否可以中止审理等。要正确处理上述种种问题,主要应把握以下两个基本思路。 (一)要牢固树立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彼此独立的司法理念 责任,不论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还是违宪责任,都是行为人在违反法定义务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责任有预防、复原、惩戒之功能。形式不同,功能亦有差别,如刑事责任以惩戒为功能主导,而民事责任则以复原为功能典型。[22]至于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二者在法的强制性与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目的性方面有着诸多的类似与趋同,但它们在强制程度、责任性质、承担方式及免除情形上的特征相异,从而构成二者于理论及实践领域相遇、竞合并适用特定处理规则的根本缘由。[23] 具体来说,作为民事违法行为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民事责任的基本目的和作用就是让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金钱性的损害赔偿,从而恢复因侵权行为而改变了的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民事责任应该遵循“无损害就无赔偿”的原则。[24]在资本市场上,证券民事责任就是从投资者损害出发,通过民事责任制度填补投资者损害。至于行政责任,它是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权而对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主体所科处的制裁或者惩罚。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所期待的行政秩序,行政责任并不局限于恢复权利义务关系的原状,甚至可以超出原来的权利义务关系去追求惩罚或者预防违法行为的目的。在资本市场上,行政责任制度主要是抑制各种不当行为以维护市场秩序,并对违法行为者施以威慑、惩罚等制裁手段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归结起来,民事责任与行政处罚的最重要的区别,主要有三。其一,具体目标上,行政处罚不是从当事人的权利出发,而是考虑是否违反相关监管规定。其二,归责原则上,民事责任中的损害赔偿是直接为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而服务的,为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目的,在民事责任的追究中,部分地采用了结果责任或者无过失责任的原则,即在特定情况下,不管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只要对他人造成了损害,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而行政责任属于公法责任,作为行政违法行为的主观要件,行为人必须具有过错即故意或者过失才承担责任。其三,在举证责任以及证明程度方面,在民事责任的追究上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在证明标准上采用“优势证据原则”,而行政责任通常由行政机关举证,且必须达到接近“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 正是由于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二者的价值取向与目标设定是不同的,导致其责任机制不同,因而二者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不是必然的联动关系或可替代关系。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即便二者基于同一事实,但完全可以两个程序同时展开进行。即便在先提起民事诉讼的场合,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判断并作出判决,不必等待行政处罚的结果。同样地,在先提起行政调查的场合,即便当事人没有提起民事诉讼,也不必等到行政调查终结之后再考虑民事诉讼。在取消前置程序后,证券民事赔偿就可以不受“先刑后民”或者“先行后民”规则的限制,“行民并用”,即对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可以分案审理,同时追究违法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二)实践中应当把握的协调问题 如前所述,行政处罚是基于行为人违反行业规范或市场规范,追究其行为不当性,不是从投资者损失出发,围绕有没有侵犯当事人的权利而展开,因此,尽管民事诉讼证据部分可能和行政处罚的有重合,但基于二者本质的差异,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认定违法行为人的虚假陈述,不能取代行政机关的调查。但是,鉴于民事诉讼证据部分可能和行政处罚的有重合,为了避免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在认定行为人虚假陈述的结论上有矛盾,从而给证券市场造成不应有的困惑和负面影响,因而,在取消前置程序后,在法院民事审判在前,行政处罚在后的情形下,在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也需要必要的协同机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正确认识民事判决与行政处罚以及行政措施之间的关系 由于民事证明标准要低于行政证明标准,因此,通常情形下,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人未必会受到行政处罚。但是,在证券民事赔偿领域,由于行为人虚假陈述只有构成重大性才能承担民事责任,换言之,承担证券民事责任的虚假陈述行为一定是具有严重性的,因此,民事判决认定构成虚假陈述的,虚假陈述行为人一般要承担行政责任,即便可能不构成行政处罚,但必定要有行政措施。但是,由于行政措施针对的行政违法行为范围很广,实践中诸多被采取行政措施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违反的是合规性的要求,并不当然涉及证券欺诈,未必造成投资者损害,所以,未必要承担民事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措施不一定有民事责任,但有民事责任必定有行政处罚或行政措施。从法理逻辑上看,这也是由于行政处罚与民事赔偿制度保护的法益不尽相同,在判断重大性问题上的出发点有差异导致的。[25] 2.建立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必要的沟通协调机制 正是因为上述二者彼此独立又有证据关联的关系,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在行政调查尚未启动或调查结果尚未公布的时候,人民法院如果确定行为人有重大虚假陈述,在民事判决后,审理法院可以提供司法建议书,告知行政机关相关案件线索及审判结果。当然,鉴于行政调查与民事诉讼不同的目标定位以及运行机制,行政机关是否启动调查以及如何采取行政措施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简单地说,二者定案的结论可以参考,但如何立案调查则彼此独立自行决定。尤其是判决之前,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一般不需要相互沟通协调,以保持独立性。但针对特殊重大案件,必要时行政机关也可以前期介入,二者就个案建立必要的沟通协调机制。 【作者简介】 【注释】 [1]《若干规定》第6条。 [2]我国设置前置程序的缘由主要在于:(1)我国证券市场处于转轨时期,需要稳定与发展,若不加限制的受理虚假陈述案件,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2)若不规定前置程序,案件数量可能过大,致法院无法处理;(3)可解决原告在起诉阶段难以取得证据的困难;(4)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专业性强,人民法院不可比拟。参见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130。 [3]《纪要》第9条关于“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案件受理”规定: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以自己受到欺诈发行、虚假陈述侵害为由,对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人以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主张的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未经有关机关行政处罚或者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为由请求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4]参见宋一欣: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J],法律适用,2003,(4):9。 [5]特殊情况下,投资者也可能在揭露日之前通过个人途径知道了上市公司造假,即便这时候投资者去起诉,就该个人投资者而言,其诉讼时效的确定法理上应以其知道上市公司造假致其利益受损起算,但鉴于证券民事赔偿纠纷是群体性案件,一个案件起诉后往往会引起巨大的连锁反应,很快会有一系列的案子起诉到法院,而这也是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与普通民事案件的重要区别。正是基于这个群体纠纷的特性以及为便于群体纠纷后续的代表人诉讼、示范判决等措施的推进,即便不同的投资者,可能各自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并不相同,但就整个证券民事赔偿案件而言,还是要确定一个揭露日,并以揭露日作为该案件所有原告(投资者)共同的诉讼时效起算日,即以大多数投资者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这样,揭露日也就成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6]孙超:证券虚假陈述中三个时间基点的意义与认定[J],人民司法,2018,(17):15。 [7]参见《孙小新诉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2014)长民四初字第77号,https://susong.tianyancha.com/15d969a851f94956bdc09db7d74511ec. [8]指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14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9]陶雨生、武峰:投资者索赔的分水岭——关于虚假陈述揭露日的确定[J],中国律师,2009,(7):25。 [10]张勇健:论虚假陈述侵权行为的几个时间点[J],法律适用,2003年,(4):8。 [11]张保生、朱媛媛:证券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及判例分析,http://www.acla.org.cn/article/page/detailById/20859. [12]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264。 [13]《证券法》第80条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 [1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第40号令,2007年1月30日公布实施。 [15]吕贤: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纠纷之“重大性”判断,https://www.sohu.com/a/418740415_654618. [16]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曾在2003年相关司法解释发布时阐明,虚假陈述所涉及的重大性问题应当在前置程序中得到解决,民事案件审理中可不涉及而当然认定。参见汤欣、张然然: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宜对信息披露“重大性”作细分审查,证券法苑,2020(28):98。 [17]薛洪增:10年,我们一起走过的维权路,证券时报,2012年3月19日。 [18]丁义平:民事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原因剖析与解决路径——以最高人民法院209个民事案例为样本 ,司法改革论评,2018,(2):45。 [19] 汤欣:《证券法》第69条有关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之研究,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评论,2009,(2)98。 [20]陈洁:证券法应明确投服中心的功能定位,中国证券报,2016年12月13日。 [21]丁义平:民事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原因剖析与解决路径——以最高人民法院209个民事案例为样本 ,司法改革论评,2018,(2):45。 [22]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96:6。 [23]胡肖华、徐靖:行政主体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竞合的数理分析[J],行政法学研究,2007,(2):35。 [24]黎宏: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适用之司法困惑与解决[J],人民检察,2016,(12):25。 [25]汤欣、张然然: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宜对信息披露“重大性”作细分审查,证券法苑,2020(28):98。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
||
|
|
||
| 【关闭】 | ||
| |
||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ICP备案号:鲁ICP备13032396号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吴泰闸路7号 邮编:27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