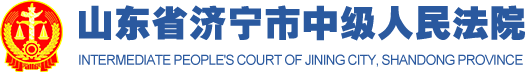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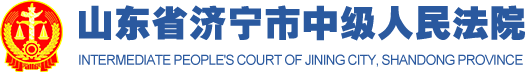
论推定的概念、性质和基础事实(三) |
||
| 来源: 发布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 ||
|
六、从一则案例来看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在推定的结构中,客观存在的基础事实(具有确定性),是适用推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对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仍存在一些不准确的认识,有必要予以澄清。以下通过一起建设工程合同欠款纠纷案的分析来解释这个问题。 (一)该案的案情及处理结果 2007年8月,某村委会将乡村公路的建设工程发包给李甲承建。李甲承接工程后,将该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按每平方米12元的价格违法分包给赵乙,赵乙又以每平方米11元的价格转包给杨丙,该村公路建设工程于同年11月完工并投入使用。工程施工期间,杨丙向赵乙要求预支工程款,赵乙遂介绍杨丙与李甲认识,要求李甲先为垫付,之后从李甲应给付赵乙的工程款中扣除。杨丙遂以借支的形式在李甲手中借款60000元以支付工人生活费及其他开支。2008年1月,李甲与赵乙结算后,赵乙出具了证明,证明内容为:“本人与李甲工程款已结清,特此证明。” 2008年3月20日,杨丙与赵乙对工程款进行结算后,赵乙向杨丙出具了欠条。欠条载明:“今欠到杨丙打路人工工资总计148500元。杨丙本人已领60000元,下欠88500元”。 后赵乙对下欠款项88500元一直未付,另外村委会尚有97860元工程款未付李甲。 杨丙遂以某村委会、李甲、赵乙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支付下欠工程款88500元。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李甲与赵乙均认可二人在结算过程中,已将杨丙向李甲借支的60000元作为李甲应支付给赵乙的工程款抵帐,杨丙出具的借条并未交给赵乙。但赵乙称其出具给杨丙的欠条中没有扣除杨丙向李甲借支的该60000元,因此其仅欠杨丙工程款为28500元。而杨丙却称,欠条上载明的“杨丙本人已领60000元”字样即是扣除的其在李甲处借支的60000元。 审理与判决。法院根据现有事实认为,杨丙向李甲借支60000元后,李甲与赵乙结算在先,赵乙与杨丙结算在后,赵乙向杨丙出具的欠条上载明的“杨丙本人已领60000元”与杨丙向李甲借支的60000元在数量上吻合,故赵乙与杨丙结算时应当一并结算了杨丙在李甲处的借支款,且杨丙在李甲处的借支款并非小数,称赵乙其算总帐时忽略了该笔款项,不符合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惯常的行为逻辑,据此法院认定赵乙应支付杨丙下欠工程款88500元。 (二)分析与评论 1.李赵杨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产生过程及其相互关系。 让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李赵杨之间的债权债务产生过程及其相互关系。首先,李从村委会那里承接了工程。然后分包给赵乙。(赵乙垫付工程款。故李欠赵的工程款。)其次,赵乙将这个工程转包给杨丙。(故赵欠杨的工程款)接下来,杨要求赵预支60000元。而赵则要求李来垫付(因为李欠赵的工程款)。于是李垫付了60000元(却是以借条的形式)。借条在李手里。 以上情况十分清楚,不存在什么疑问。 2.本案中,当杨丙向法院起诉之后,李(作为被告之一)没有拿借条向杨提出还款的请求,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 胡文说:在本案件中,“应当说,李甲用杨丙借支的60000元抵付欠赵乙的工程款是李甲和赵乙均认可的事实,赵乙与杨丙结算时欠条注明“杨丙本人已领60000元”的事实是有证据证明的事实,这两个事实,都具备基础事实的可靠性特征。” 鉴于本案中李没有拿借条向杨提出还款的请求,这一事实说明“李甲用杨丙借支的60000元抵付欠赵乙的工程款是李甲和赵乙均认可的事实”,是真实的。60000元是用来抵付欠赵乙的工程款。这说明,赵于2008年1月之前,已经向杨支付了60000元。这个事实,通过(借条、李甲和赵乙的认可)足以认定,毫无疑问。 3.本案有哪些证据?其特点是什么? 在本案中有若干书面证据和当事人的口头陈述。书面证据有(1)借条;(2)一张证明;(3)欠条。此外有当事人(李赵杨)的口头陈述。 以上3个证据事实有何特点呢?仅仅从3个书面证据本身(假如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的话)来看,它们具有如下特点:(1)借条(发生在李甲与杨丙,没有赵乙参与。杨从李那里借钱60000元,出具了借条,这借条保存在李手里。)(2)一张证明(发生在赵乙与李甲之间,没有杨丙参与。)欠条(发生在赵乙与杨丙之间,没有李甲参与)。 4.关于欠条“杨丙本人已领60000元”的问题,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2008年3月20日,即出具借条2个月之后,赵向杨出具了欠条。欠条载明:“今欠到杨丙打路人工工资总计148500元。杨丙本人已领60000元,下欠88500元”。 不仅如此,杨丙在法庭的口头陈述中说,“欠条上载明的“杨丙本人已领60000元”字样即是扣除的其在李甲处借支的60000元。”杨承认60000元是当初扣除的(从李那里借支的)。杨的口头陈述话与欠条记载之间有矛盾吗?没有。可以看作是对欠条记载的一种合理解释。 反观赵乙,其陈述前后矛盾。胡文说,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李甲与赵乙均认可二人在结算过程中,已将杨丙向李甲借支的60000元作为李甲应支付给赵乙的工程款抵帐,杨丙出具的借条并未交给赵乙。 它意味着,杨的取钱行为具有如下两个后果,第一是抵账。李甲实际上向赵抵付了60000元工程款。假如李以前欠赵60000元工程款的话,杨从李那里取走60000元只后,李就不欠找一分钱。李赵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那张证明就记载了这一事实。)第二,由于这60000元是杨从李那里拿走的,等于说赵已经向杨支付了60000元。假如赵欠杨的工程款总额是10万元,那么,扣除这60000元之后,还欠杨40000元。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赵乙称其出具给杨丙的欠条中没有扣除杨丙向李甲借支的该60000元,因此其仅欠杨丙工程款为28500元。”这话毫无根据。无法与前面的话自圆其说。明明扣除了,怎么说没有扣除? 5.杨丙有收回借条的必要吗? 没有。因为,第一,李赵均认可(当事人的陈述),是抵付赵乙的工程款。第二,李与赵之间有一张证明(书证)。胡文说,2008年1月,李甲与赵乙结算后,赵乙出具了证明,证明内容为:“本人与李甲工程款已结清,特此证明。”第三,李本人认可。李甲与赵乙均认可二人在结算过程中,已将杨丙向李甲借支的60000元作为李甲应支付给赵乙的工程款抵帐。(这60000元是李欠赵的工程款的一部分。) 以上三个证据形成紧密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杨不欠李的任何钱款。因为这60000元是杨(从赵处)应得的工程款的一部分。由于李欠赵的,故赵请求李代为支付。 6.如何理解胡文所说的“双方均没有书面证据证实”? 胡文说“双方均没有书面证据证实”,需要证实什么?对此应如何理解?我们知道,“杨丙本人已领60000元”,是赵乙给杨丙出具的欠条上的一句话。对于欠条上的这个事实,胡文说“双方均没有书面证据证实”。为什么一定需要书面证据来证实呢?口头陈述为什么不可以?胡文没有给出理由。 原告杨丙在法庭的口头陈述中说,“欠条上载明的“杨丙本人已领60000元”字样即是扣除的其在李甲处借支的60000元。这是当事人之一(杨丙)的承认,是一种有力的证据。 然而,被告赵乙不同意原告的说法,于是他申请了一名证人作证,但未被法院所采纳。(据胡文说,“在上述案例中,赵乙曾申请其与杨丙结算时在场的一个证人出庭作证,证明赵乙与杨丙将人工工资结算后,赵乙将手中的领款条据已交还给杨丙的事实。法院在认定证据过程中,认为证人陈述的事实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且证人未参与结算的全过程,没有采信该证据。”) 从上面可以看到,在欠条的“杨丙本人已领60000元”问题上原被告双方均有证据,只是被告方证据力弱,被法官排除了。原告的证据是有力的,故被采纳。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符合推定的适用条件。只能采用举证责任规则,驳回被告的证据,采纳了原告的证据。可见,在欠条问题上,法官并没有采用推定的方法。这种处置是合理的。胡文说:“本案中法院认定赵乙出具的欠条上扣除的60000元和杨丙在李甲处借支的60000元为同一笔款项的事实,是通过推定进行认定的。”这是误解。 假如在欠条的“杨丙本人已领60000元”问题上双方均没有证据,那么可以采用推定的方法,假定一个事实(推定事实)存在。但在本案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条件。 (三)关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上述案例中,胡文指出:“法院认为杨丙在李甲处的借支款并非小数,赵乙称其算总帐时忽略了该笔款项不符合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惯常的行为逻辑,该种推定更是将行为逻辑的模式概念强加于赵乙,对赵乙是不公平的推定,因为杨丙同样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若其与赵乙在结算时已将债权抵付工程款,其应当要求收回借条,在不能收回的情况下,应当在欠条上注明已领取的60000元为抵帐而来,这样即使将来李甲再持借条向其索要借支款,其也可以向赵乙追索。因此,本案例的推定事实与基础事实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不具备高度盖然性。” 从上面可以看到,胡文在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应该存在必然的联系;第二,这种联系应该具有高度盖然性。让我们对此加以分析。 1.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应该存在必然的联系吗? 毫无疑问,在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的性质是什么?是必然的联系,或者可能的联系,或者其他的联系?这是需要认真加以分析的。 《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典》第600条规定,推定就是根据另一事实的证明力或若干事实的总和,假设某一事实的存在。根据该规定,所谓推定事实是指“假定的事实”。它不是像严格的逻辑推理那样得出的具有必然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联系,而是一种(有一定客观性存在的)可能的联系。正因为这样,当推定事实做出之后,受不利益的一方,如果发现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即可对推定事实予以反驳和推翻。因此,作者在这里所讲的“必然的联系”是不准确的。 如果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只有“必然的联系”(唯一正确答案),那么,推定的适用范围将受到很大限制。 2.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应该具有“高度盖然性”吗? 按胡文的原义,基础事实不等于推定事实,这是常识。盖然性即可能性。胡文认为,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应该具有“高度盖然性”。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从基础事实到推定事实之间不存在高度的可能性。即便存在可能性,哪怕微弱的可能性,也是允许的。以推定死亡为例,在死亡事实与推定死亡之间的联系,不一定非得需要“高度的可能性”。因为推定事实是假定的事实。从基础事实到推定事实,有时具有很高的可能性,有时仅仅具有(假定的)可能性,并不具有很高(或高度)的可能性。因此,把“具有高度盖然性”作为本案适用推定的条件,未必合适。 七、总结与建议 以上我们讨论了推定的概念和性质,讨论了法律推定的基础事实、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以及它们的性质,还讨论了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从提高司法效率的角度讲,推定(与使用证据相比)具有很大优势,因此在现代司法实践中,推定的运用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针对这种汹涌而来的趋势,我们更应当重视它的缺点,尽量避免和消除其副作用。为此,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运用立法手段,对推定的概念和性质作出规定,使它在推定的司法实践中,像一盏明灯一样指引人们前进的方向。 二是从法律上对基础事实的性质作出规定。如在法律或者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必须具有客观性。前面已经论述过,在事实推定中的基础事实,客观性是其唯一的性质。与法律推定的基础事实(其性质是法定性和客观性)相比,这种性质无疑显得十分脆弱,因为这种性质缺乏法律的保障,全凭办案人员的主观自觉,而现实表明,这种“主观自觉”是非常靠不住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思想上特别重视它,还建议立法机关就此做出规定(事实推定中的基础事实必须具有客观性),否则难以为大量的司法实践提供基本的准则,难以遏制办案人员任意制造基础事实的行为。 对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的性质作出规定,为法官作出正确推定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可以排除“想当然”、“拍脑袋”、“轻率电话取证”“视频取证”等主观主义行为而获取和采纳的所谓“基础事实”,对于确保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的牢固性,具有极大的意义。 同理,对法律推定的基础事实的性质也要做出明确规定。 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编印指导性案例(关于法律推定的基础事实和事实推定的基础事实的案例),并加以适当评论后下发,指导法官们合理推定。 四是对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之间的冲突作出规范。有人或许会说,在烟灰缸坠落伤人案件中,关于侵害人范围的推定,是法院依据职权作出的事实推定。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因为它有意忽略了一个前提,即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既然已经有法律规定,法官就不能有意忽略之,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在有法律推定时,不能规避它去做事实推定。 五是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并非必然的联系,而是存在一定客观性的可能的联系。这种可能性的要求亦并非“高度的”,只要达到一定程度即可。 最后,谈一下新型取证方式所获得的基础事实问题。 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取证方式不断出现。如时下兴起的网络视频可以为人们远距离通讯提供极大地便利。但是,有人发现这种视频可以被人为更改,而不留任何痕迹,可以任意根据使用者本人的需要进行编辑组合,以假乱真,欺骗性很大。如果我们轻易认可这种新形式作为证据,或者认可采用这种方式所获取的“通讯内容”,那么人们就可以轻易地制造所谓“基础事实”。这显然是危险的,应当受到禁止。对此,我国公证机关要求使用者到公证机关现场,予以公证,以确保其真实性。 这里实际上还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涉及传统证据方式与新型证据方式的关系问题。对于后者,我们当然不能轻易排斥,但也不能立即允许,需要在一定期间对它加以考察和完善。对于前者,因其在以往的一定时期内起到了行之有效的重要作用,社会公众已经广泛认可,因此,我们在找到一种可以有效代替它的新证据方式之前,不能立即废除,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由此可见,网络电话也好,网络视频也罢,绝不可轻易被接受为基础事实的取证方式。目前它们不能破坏传统的久经验证的取证方式。
作者:叶自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法律适用》2021年第9期 |
||
|
|
||
| 【关闭】 | ||
| |
||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ICP备案号:鲁ICP备13032396号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吴泰闸路7号 邮编:272001